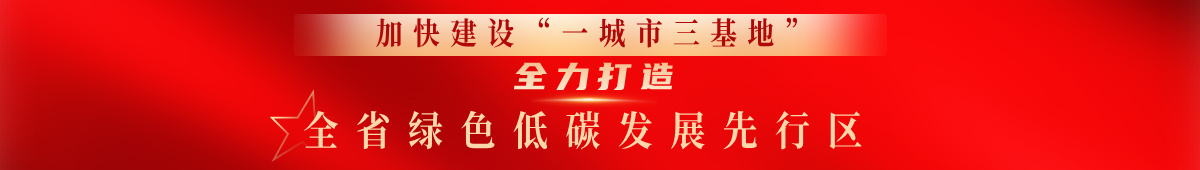惠亭山的草木枯荣依旧,溾水潺潺不减当年。踏着聂绀弩先生曾涉足的阡陌,忽生一念:尚若这尊以笔为刃的“卧佛”尚在,听王立平先生《葬花吟》之凄切,闻刘炽前辈《英雄颂》之雄奇,会如何落笔?
人生本是一场向死的旅程,这是无需辩驳的宿命。帝王将相的陵寝与贩夫走卒的坟茔,最终都归于尘土;金樽玉食的奢靡与箪瓢屡空的清苦,终点都是生命的寂灭。曹雪芹写《红楼梦》,究其根本,便是勘破了这层宿命,将满腔悲悯注入字里行间。《葬花吟》之所以能穿越百年仍动人心魄,不在辞藻的清丽,而在其对“悲情”的独特解构——林黛玉荷锄葬花,绝非闺阁女子的无病呻吟。
“侬今葬花人笑痴,他年葬侬知是谁”,这问句里藏着对生命最深刻的敬畏。当旁人将落花视作废弃物,任其被践踏碾压时,黛玉以锦囊收之、花锄埋之,用一场郑重的仪式,赋予落花与人类同等的尊严。这不是“痴”,是对脆弱生命的共情;不是“愁”,是对美好消逝的珍视。王立平先生耗时一年零九个月打磨旋律,想必也是参透了这份深意。他的《葬花吟》没有堆砌悲戚的音符,而是以沉缓的节奏模拟葬花的步履,用颤栗的旋律呼应生命的悸动——悲情至此,已然升华为对人性的礼赞。
若说《葬花吟》是江南烟雨里的一缕愁思,那《英雄颂》便是北国疆场上的一声长啸。上甘岭的焦土之上,炮火吞噬了无数年轻的生命,幸存者的战栗足以印证战争的残酷。但人类的伟大,正在于能从极致的悲怆中淬炼出崇高。电影《上甘岭》剥离了战场的血腥,提炼出杨德才舍身炸地堡的英雄形象;刘炽则以旋律为剑,劈开死亡的阴霾,让人性的光芒直射而出。
《英雄颂》的激昂,从不是空洞的口号。它的悲壮,藏在战士们写家书时的温情与赴死时的决绝里;它的力量,源于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”的正义坚守。那些昨天还念叨着“山里野果甜”的青年,今天便愿以血肉之躯筑成防线——这种将个体生命融入家国大义的选择,正是人性之美的另一种极致。刘炽的旋律之所以至今无人超越,恰是因为他抓住了“悲壮”的内核:不是死亡的惨烈,而是生命的重量。
初看之下,黛玉葬花与杨德才赴死判若两极:一者纤弱,一者刚猛;一者悲戚,一者激昂。但细究便知,二者同源于对生命的敬畏——黛玉怜落花之脆弱,是“小爱”的极致;英雄护家国之安宁,是“大爱”的升华。两种悲情,两种坚守,却在“人性之美”的坐标上达成了统一。这恰如吴晗先生评史时的洞见:世间万物纵有表象之别,内核的善恶是非终有定论。
而串联起这两种美的,正是文化的力量。若没有曹雪芹,黛玉的花锄早已朽于尘土;若没有刘炽,英雄的呐喊早已湮于炮火;若没有历代文人墨客与艺术创作者的坚守,那些藏在悲情里的人性之光,早已消散在时间的长河中。他们以文墨为舟,以音符为帆,让脆弱的生命与崇高的精神得以跨越时空,成为滋养民族心灵的养分。
暮色中的惠亭山愈发沉静,溾水倒映着星河。此时再听《葬花吟》与《英雄颂》,已不觉得悲戚。因为明白:人生的宿命或许是悲情,但人性的光辉能让悲情生花;个体的生命终将消逝,但文化的传承能让精神永生——这便是世间最深刻的道理,也是人性之美最动人的模样。(何永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