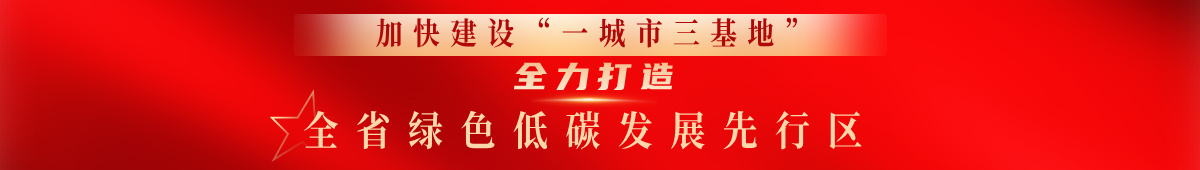京山西南,司马河弯着腰流。河岸边那片土,踩上去发沉——不是土湿,是装着太多年月,压得人不敢轻举妄动。
五千年前,这里就升起人间烟火气。不是烧荒,是架着陶窑,捏出碗罐,再往田里插稻秧。先民们没留下名字,只把陶片埋在地下,把稻壳掺进土里。如今锄地,偶尔能碰着带纹的陶片,指尖一摸,还能感觉出远古窑火的温度。那不是古董,是故土的骨头——它最早就是靠着这些,把“活着”的样子刻进了我的皮肉里。
后来到了两千多年前,这片土地上就有了刀光。孙武、伍子胥在这里摆过阵,兵戈相击的声儿,该是渗进了河底的沙。更让人记挂的是沈尹戌,提着剑为国战死于斯。没人知道他埋在哪棵树下,但走在这片地上,总觉得每根草都直着腰——那是替他把英名撑着,不让风刮散。英雄不一定要有坟茔,故土会把他们的骨头收着,再长出新的庄稼,新的人,把“忠烈”二字悄悄传下去。
下洋港那片阔大的故城遗址,看着是平的,地下全是故事。挖开一层,能看见先民的灶坑;再挖一层,或许是战国时的瓦当。不是考古队来,没人敢随便动土。不是怕破坏文物,是怕惊着地下的魂灵——他们在这儿住过、吃过、哭过、笑过,故土把他们的日子原样存着,像存着一坛老酒,越久越醇,越不敢轻易掀开盖子。还有五姊堆,立在山头俯视过云梦古泽,堆上的土都带着迷。多少年没人说清它是怎么来的,也不用细说。故土总有些话不直说,留着迷团,是让后人别太轻狂——你以为懂它,其实它藏着的往事,比你知道的多得多。
丰谷、丰茂街、石龙过江、太子山等,这些名字不是随便叫的。丰谷堆里,藏着先民的汗;丰茂街上,走过后人的脚;石龙过江的石缝里,还留着当年李先念、张体学挥锹奠基的脚印;太子山的树,该听过多少代人的家长里短。这些名字不是符号,是故土的皱纹,每一道都记着事儿——它不喊疼,也不炫耀,就这么把往事裹在皱纹里,等着有人慢慢看,慢慢懂。
我总不敢在这片地上快跑。怕踩疼了地下的陶片,怕惊着沈尹戌的魂,更怕辜负了它。五千年来,它养着稻子,养着陶匠,养着英雄,也养着像我这样的平庸之辈。它不说话,却用每一粒土、每一条河、每一个地名,告诉我们:你是谁,从哪来。
这片土地,不是用来炫耀“古老”的,是用来敬畏的。敬畏它装着的五千年,敬畏它护着的英魂,敬畏它把日子过成了历史,又把历史酿成了根。走得再远,一想起司马河畔那片沉实的土,心里就有了底——那是故土在牵着你,不让你忘了本。(何永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