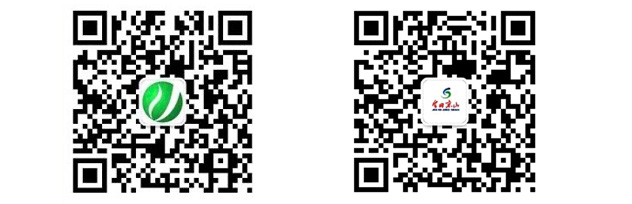我在宋河插“醉”秧(文/王章一)
时间:2024-05-10 来源:京山市融媒体中心
四五月间,田野里到处都是春天的信息,泥土的芳香。这是春的世界,也是"酒"的世界,令人陶醉。然而,在六七十年代那年头,却偏偏缺酒。 那时,我在生产队劳动,由于从小就跟随母亲学稼,到了"弱冠"之年,已初步成了一名操作庄稼活的"全能选手"了,其中插秧这项,还是队里的"男子单打冠军"呢。 记得1968年开秧门的那天,天气真好,春日融融,春风微微,明镜似的水田里风平浪息,象个待嫁的处女,又象激战前的战场,显得那样安静。 中午,队长邵海涛叫收工回家吃饭时,我的一个本家叔叔王明清三把两把地洗了一下腿上的泥水,走到我跟前,悄悄说,章一,就到我家吃饭去,免得回家一去一来走冤枉路。我知道,明清叔的家离这插秧的地方最近,他的村子叫"红玉湾",只有他一户人家,老伴早故,儿子章斌是亦工亦农,在宋河粮管所上班,女儿章秀在家种田,还未出嫁。好似独立王国。 明清叔的午饭还挺丰盛,一大碗煨莴笋,是从灶膛一个窑罐里拖出来倒在碗里的,里面交了几片腊肉,汤水上还漂着一圈草木灰,象撒的胡椒粉,但气味香极了。明清叔还特地煮了几个咸鸡蛋,加上腌菜辣椒豆瓣酱之类的常备菜,也凑上了"四菜一汤"。但,最令我咽口水的,是明清叔端出了两茶盅酒,一盅足有半斤之多。 那时的酒是稀有之物,私自酿酒也是违法的,要是被干部知道了,就会当"阶级斗争新动向"来抓,或"资本主义尾巴"来剁。因此,平时难得有此口福,只是过年才沾一点点,一户凭票供应才买几斤酒,还是"土茯苓"酒,喝了锥头,脑壳疼,主要用来待客。客人也不敢放量喝,自己从来不晓得醉酒是啥滋味。明清叔充分利用他这山高皇帝远的地理条件,从自己的口粮中抠出了一点,偷偷地酿了点酒过忙月。 "来,我俩一人一盅,喝干了吃饭。″明清叔眯眯地笑着说。我端起酒蛊就呷了一口,品了品,略带糊味儿,正宗的纯粮食酒,连忙说,好酒好酒!明清叔见我喝得津津有味,并还称赞了他的酒,笑得格外地开心。 离开明清叔家,自我感觉良好,第一个下田插秧插了几十米远,队长海涛哥和社员才陆续下田。渐渐的,渐渐的,酒精的作用上来了。不知是我在旋转,还是天地在旋转。但,我插秧的意念丝毫没有动摇,左手紧握秧头,右手好似蜻蜒点水,解秧头时,也没伸腰。那块水田叫"弯五斗",又弯又长,不比500米的跑道短。我飞快地在醉眼朦胧中划水放绿,在拖泥带水中抽脚后行,将依次下田的男女老少甩在远远的前面。 这时,队长海涛哥在田埂上打秧头时见了,高声喊道:"瞧呀,章一的秧插得又快又好!"啊,轻易不表扬人的队长夸奖了。我没想我的插秧技术今天发挥得这样好。难怪,京剧里有曲戏,叫《杨贵妃醉酒》,说的是贵妃娘娘醉酒后的舞姿格外的美;还有,大诗人李白醉酒吟诗,成为千古美谈;我王某人醉酒插秧,说不定也是一段佳话呢。看来劳动和酒的结合,竟出现了一种浓郁的艺术意境,一种缠人的艺术魅力。我第一次感到了日复一日、口朝黄土背朝天的繁重辛苦的劳动也如此般的怡悦。 这是我人生中喝酒史上的第一次醉酒,那醉的意境却够我回味一生了。 (责任编辑: ) |
|||
|
- 上一篇:旅社住宿趣闻(文/王章一)
- 下一篇:山中飞出的歌